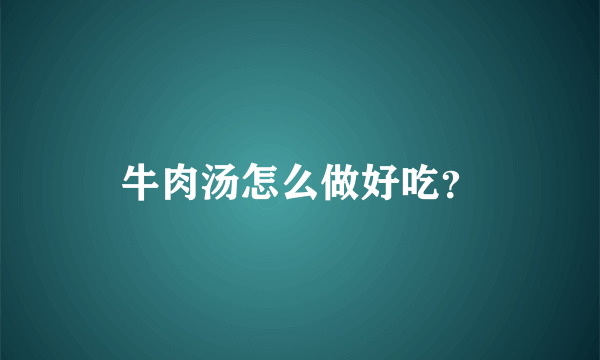晚年马洛伊
《一个市民的自白》开篇介绍的考绍市容。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描写的中央广场,他少年时代在家里窗口前俯瞰的“大世界”。
世界公民马洛伊·山多尔,1900年出生在奥匈帝国时期的匈牙利王国,从血缘上说是匈牙利族;一战后帝国解体,一纸《特里亚侬条约》将他的家乡考绍划给了斯洛伐克,当时正在德国读书的马洛伊一下子变成了没有家乡的人。19岁开始游学欧洲,先去了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和法国巴黎,28岁才回到匈牙利。接下来的二十年他住在布达佩斯,经历了二战空袭和冷战独裁,48岁去国后再没有回去。他去了苏黎世、日内瓦和那不勒斯,52岁移民美国直到89岁自杀。
马洛伊不仅走遍了世界,而且住遍了世界。但不管他流浪到哪里,都在灵魂深处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家乡。当然,对于马洛伊这样一位世界公民来说,“家乡”的概念是需要注释的:从地理上讲,马洛伊的家乡是考绍,尽管他从青春期开始就试图逃离。从文学生涯上讲,马洛伊的家乡是布达,是他曾经隐居了二十年的克丽丝蒂娜城区。
但即使住在克丽丝蒂娜城区,即使已成为有地位的作家,他仍觉得自己是“只打算在这里小住一二十年的赶路者”,对他来说,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的家乡——匈牙利语。在后半生的流亡岁月里,他始终坚持用母语写作,他拒绝回到仍不自由、仍不独立的祖国,只将语言视为自己名副其实的家乡。
《烛烬》
是友谊的一曲挽歌,也是颂歌
在译林今年推出的三部马洛伊作品里,我首先想谈的是《烛烬》,这部书写于1942年,是马洛伊作品中被译成外语种类最多的一部,各国出版社推出马洛伊,大多都从这本书开始。可以这么讲,《烛烬》是马洛伊一生56部作品里语言最精美考究、风格最强烈的一部,当然,对我这个译者来说,翻译这本书也最耗神耗力,大段哈姆雷特式的独白,经常要反复朗读一遍遍修改,根据朗读的感觉加字减字或调整语序。比如描写山林里的黎明这一段:
“天已经不黑,但也不亮。在那一时刻,森林的气味是那样冷峻、粗粝,仿佛所有的有机生命体都在世界的大卧室里开始苏醒,发出隐秘而邪恶的叹息,不仅是植物和动物,人也一样。就在这时,起风了,风吹得舒缓,如同苏醒时的轻叹,忽然意识到自己降生的世界。地上散发着湿草、野蕨、树苔和由腐烂的果实、落叶、松针织成的柔滑地毯混合了林间雨露的气味,犹如从情人身体上散发出的激情的汗味。这是一个神秘的时刻,是古人和异教徒在丛林深处张开手臂,面向东方,怀着诱人的期待虔诚祭祀,以求理性与心智之光能够在物质性的心脏与世界中获得永恒的时刻。”
《烛烬》的故事简单而深沉,讲两位四十一年未再见面的72岁老人并非意外的重逢,为了了却折磨彼此一生的心事,回忆四十一年的一次止于动机的谋杀。亨利克将军是匈牙利族,也是奥匈帝国的遗老,一战后隐居在家族的庄园和猎宫里,孤独地厮守着帝国时代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质,用距离抵抗世界的变迁。在二战期间,将军青年时代的好友康拉德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穿越欧洲战场来探望他,两人彻夜长谈,从点燃很粗的、教堂使用的蓝色蜡烛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根蜡烛燃尽。
说是交谈,实际主要是将军讲,客人听,从童年时代的友谊开始,到青年时代的形影不离,到将军发现自己的朋友和妻子有染,到康拉德因动杀心而畏罪出逃,到女人在相敬如宾的婚姻里抑郁而亡……这个故事听上去像老掉牙的三角恋,但实际上讲述的是男人间的友谊。在十万字的小说里,仅将军一人的表述里,“友谊”这词就使用了百次。
当然,亨利克将军讲述并恪守的友谊,不是我们现当代人理解、体会、认为的那种,而是帝国贵族恪守的一种品质、精神和法则。甚至在将军看来,是高于爱情的。少年时代,亨利克和康拉德好得就像单卵的双胞胎,他俩的友谊既不同于彼此想要占有身心的欲情,也不同于滑稽而郑重的结拜兄弟,“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那么严肃而沉默。就像所有触及生命本质的伟大情感那样,也包括了羞惭和自罪感。一个人不可能毫无自罪感地将另一个人从他人的手中夺过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亨利克注意到了自己与朋友的差别。康拉德出身于贫寒家族,他嫉妒亨利克身上自己没有的东西,嫉妒他的富有、慷慨和自信。亨利克意识到这一点后,努力放下身段,蔑视财富。亨利克结婚后,康拉德天天来庄园吃饭,一起到林中打猎,直到有一天亨利克无意中发现,朋友曾将枪口对准自己……从那之后,亨利克陷入了后半生的痛苦,不仅失去了友谊,也失去了爱情,他终于痛苦地正视了以前不肯正视的现实:阶层和教养的差别是很难逾越的,他没有想到朋友会将嫉妒发展成蔑视,甚至憎恨。
但是即使这样,亨利克将军并没有记仇,而是用他贵族的品质谅解对方:“当我有一天开始沉浸于心灵和书籍之中,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时光流逝,生活在我的周围变得晦暗朦胧。书和记忆越攒越多,越积越浓。每本书里都有一点点真相,所有的记忆都表明,人们徒然知道人际关系的真正本质,他们不会由于各种见识而变得更加明智。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向我们曾经视为朋友之人索求真相与忠诚,哪怕有许多件事表明了这个朋友的不忠。”
彻夜的长谈,以康拉德告别结束,尽管客人没有承认或否认什么,但是读者明白,最终还是“友谊”获胜。对友谊的背叛,虽然让他俩都输了一生,但至少在风烛残年时揭开了秘密,了结了恩怨,他俩都能带着旧时的“友谊”平静地死去。也许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谈论这种友谊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想,也恰恰由于这种不合时宜,阅读《烛烬》才更有意义。想来,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憧憬,梦想,怀揣过与之类似的情感,哪怕片刻的唤醒,也是一种洗涤。高尚的情感不会因为不合时宜而贬值。《烛烬》是对友谊的挽歌,也是颂歌。
由于马洛伊很早开始流亡,流亡中坚持母语写作,而他的作品在匈牙利长期遭到封禁,所以很晚才被国际书业发现。《烛烬》最先被译为意大利语是在作者去世近十年后,随后英文版、德文版相继问世,其他的作品也迅速传遍世界。台湾也于2006年出版了从意大利语转译的繁体版,在华语读者中影响甚广,但由于转译,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译、误译和猜译的问题。首先将作者名译为“桑多·马芮”,既不符合匈牙利语发音,也按西方语言习惯误将姓名颠倒,要知道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先、名在后的欧洲民族,“马洛伊”是姓,“山多尔”是名。另外繁体版将书名译为《余烬》是不对的,这本书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csonkig égnek,意思为“蜡烛燃烧到了根部”。蜡烛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从点燃蜡烛迎客讲起,到蜡烛熄灭送客结束,两位四十一年未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聊了他们一生的沧桑。《烛烬》最贴近原文原意,《余烬》让人联想到烬火的余热,少了“烛”字,意思偏差很大。译林出版的所有马洛伊译本都是从匈牙利文直译的,力求精准,贴近原文,尽量再现原著语言的文学性。
《烛烬》还被多次改编成电影、话剧和广播剧。我希望,它能通过我的翻译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让读者通过阅读留下一些。
□余泽民(匈牙利语翻译家、马洛伊作品中文译者)
(下转B07版)